公元260年6月2日,正是三国末期,整个中原大地被划分成了魏、蜀、吴三个国家鼎足而立:北方的曹魏政权最为强大,由魏王曹操建立,已历经三世,但不久之前却被家臣司马氏政变夺权。西南的蜀汉,开国之君是刘备,在与吴国的战争后病亡,托孤于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亮死后,如今只剩下一个昏弱之君刘禅。东南的吴国,奠基者是孙坚,大部分时间都偏安一隅,存在感不高。三个国家屡屡战乱,彼此各不相服。
然而,此时的魏国王宫中,一切却剑拔弩张了起来。
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!我宁可死,也不愿坐困受辱,还请各位爱卿助我一同讨贼!”
说这话的正是魏国第四位皇帝——年仅19岁的曹髦(máo)。而他所提到的“司马昭”,正是如今一手遮天,把持朝政的权臣,也是逼他成为傀儡的始作俑者。
话说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,之前装疯卖傻,扮演了几十年魏国的大忠臣,终于还是在自己七十岁时发动了“高平陵政变”,大逆不道地窃取了梦寐以求的魏国大权。而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更是亲手废掉了前任皇帝,扶植曹髦顶替。之后司马懿和司马师相继病亡,大权传到了司马昭手中。
自从上任第一天起,曹髦便对司马家充满了怨恨与警惕,也学起了司马懿的“隐忍”之术——收敛锋芒,却藏剑于心。
曹髦十分努力上进,经常前往太学与众学者一同讨论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等儒学经典,而他的学问与见解也令很多学者都自愧不如。但他虽然博学,却有一个致命缺点——急躁而缺乏耐心。每次召见大臣都恨不得对方能够立刻站在自己面前。所以他的重臣们都得备好车马、随时待命,一经召见,就得马上一路小跑地前往。
也正是因为这个缺点,才让他此时急不可耐地想要除掉司马昭。
“当年司马懿推翻了我们曹家,如今我曹髦也要以牙还牙!你司马家能做到,我一样能做到!”
于是曹髦穿好盔甲,登上战车,大声疾呼着就要冲杀出去。
手下大臣拦路死谏:“陛下不可冲动!如今兵马钱粮都在司马昭手中,朝中的文武官员也早已为他所用。我们兵又少,武器又弱,如何以卵击石?”
但令他没想到的是,那些久经生死的老臣都害怕的司马家,这位十九岁的皇帝却不怕,那么多人都选择向现实投降,这位十九岁的皇帝却还没有放弃——可见他并非那些软弱的亡国之君所能相提并论。
曹髦果然不听他的劝阻,头也不回地领着身边仅有的侍卫冲上了街,直冲司马昭的府邸。
杀!!!
震彻天地的喊声回响在魏国的土地上。
都说杀红了眼,然而此时的曹髦虽然还未与敌拼杀,却也已红了眼。他的心中只剩下取司马昭性命这一件事,所以无论路上惊慌的百姓还是左右生死与共的下属,他都无暇注意,只是一路策马飞奔。
突然,前方战马一阵嘶鸣,整个队伍都停了下来。
“怎么回事?”曹髦勒动缰绳,驾马向前探去,只见一个面露凶光的将军挡住了去路。
此人正是贾充,司马懿的心腹。他看到披甲带剑的曹髦起先也是一惊,不过立马恢复了冷静,命令手下开始作战。
于是双方你来我往,刀剑相向。然而兵力悬殊之下,曹髦一方逐渐不支。
眼见左右所剩无几的将士一个接一个倒下,曹髦只好亲自拔剑向前,然而贾充的将士却都不敢对他兵刃相向,甚至有人弃剑而逃。
于是战局又开始向曹髦有利的一方转变。
眼见无人敢于出手,贾充突然叫道:“成济何在?”
“末将在此。”队伍中出现了一张坚毅的面庞。
“司马公平日厚待你们这些死士,可知为何?”
“就是为了今天!”成济边说边拿起“戈”——一种尖锐的长柄兵器,向曹髦走去。
“逆贼,你敢?”曹髦怎么也无法相信,自己这句话还没有说完,就有一股热烈的东西从身体里喷溅而出,紧接着就动弹不得了。
“皇上死了,皇上死了!”左右大惊失色,百姓惊嚷叫喊,整个街市顿时乱做一团。
——自古弑君者虽然不少,但敢当街弑君的却没有几个。
听闻此事的司马昭惊慌失措地赶往现场,一把扑到曹髦的尸体上嚎啕大哭。
“臣有罪!臣有罪!臣不能保护好国君,以致陛下枉死,还有何面目面对天下?”说罢哭到晕厥,醒来后还一直说要追随曹髦而去。
司马昭是虚伪的,他的表情与内心总不能完全一致——明明比谁都高兴,却还要假惺惺地演上这一出,之后还要例行公事地召集群臣审理本次弑君一案。
当尚书建议严惩贾充时,司马昭立刻瞪他一眼以示威慑:“贾充是我的心腹,先生还是令谋处置吧。”
于是只好让成济当了替死鬼:谋弑皇帝,大逆不道——夷灭全族。可怜他对贾充和司马昭忠心耿耿,言听计从,最终却落了个全家死光的下场。
而曹髦的一生也在这最后的轰轰烈烈之中落下帷幕。虽然他没有得偿所愿,也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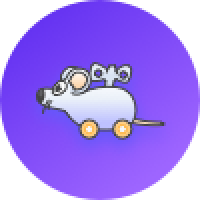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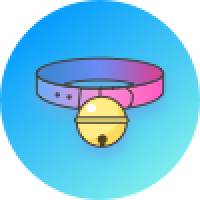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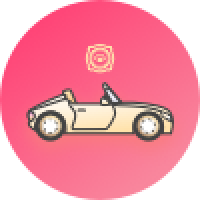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